唐詩不僅是詩歌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,亦是人類文明的珍貴獻禮。本課程的目的並非對詩人、詩歌作一般性的概論,而是以專題的方式抽繹由初唐到晚唐詩歌的許多面向,除了釐清傳統文學史中對部分詩作的誤讀與偏見,更引領大家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諸位著名詩人,如:陳子昂、王維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隱等。 初唐的陳子昂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〈登幽州臺歌〉外,文學史上總將陳子昂形塑為復古派的健將,其師法漢魏古調的精神,六朝靡麗遺風彷彿在陳子昂的主張下開始動搖。然而,陳子昂真的完全反對六朝,以復古為目標嗎?在現存的文獻當中,是否有其他的依據? 至於一向被目為「自然派詩人」的盛唐詩人王維,其實詩歌成就寬廣深厚得多,歷來吟誦不已的名篇屈指難數,其中,〈雜詩〉三首之二作為漂泊他鄉之作,「來日綺窗前,寒梅著花未」是否有其他深意?王維遇到久別的鄉親時,問的為什麼是「寒梅著花未」呢?另外,飄逸不羈的詩人李白,在宮中留下的名篇〈清平調詞三首〉,究竟「可憐飛燕倚新妝」一語有何深意?是否真有諷刺楊貴妃的意思?這組詩的主旨究竟何在?再者,婚戀是每一個人生命中的內容,但隨著時代與個性的不同,詩人對妻子的描繪也大異其趣,「詩聖」杜甫除了憂國憂民、沉鬱頓挫的一面,在較不為人所知的〈月夜〉詩中,杜甫又是怎麼看待他的妻子? 還有,中唐詩人白居易的〈琵琶行〉是歷來傳誦不已的名篇,但「琵琶女」的造型仍有值得深入研究之處,且白居易在〈琵琶行〉中如何傾注他的「投射心理」?最後,晚唐詩人李商隱,其〈錦瑟〉風靡無數讀者,此詩亦為詩人晚年對一生的回顧,隱含了理解其性格特質的鑰匙,而末聯「此情可待成追憶,只是當時已惘然」的傳統解讀多有謬誤,其真正涵義為何?當將在唐詩的課程中一一釐清。
1-3-1 李白版的中國詩歌史

Loading...
Reviews
4.9 (570 ratings)
- 5 stars92.63%
- 4 stars6.84%
- 3 stars0.17%
- 2 stars0.35%
II
Apr 4, 2021
很棒的學習,增加生活樂趣
讓我重新認識中國的文學藝術和古人的生活
古老的中國擁有太多精緻有趣的文化
我喜歡這種自由自在又有一個小目標的學習
學習,讓我的退休生活有很好的方向...
學習,讓我的精神生活像雲一般的變化多彩。
謝謝。
MM
Oct 7, 2020
算下来从《红楼梦》开始,听欧丽娟老师的课已近十年,把她的“中国文学史”课认认真真记笔记停下来,应该已经可以说自己是欧丽娟老师的学生了。跟老师学了很多东西,学到了很多治学和思考方法,解决了许多迷思和误解。谢谢老师。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听老师后半段的“中国文学史”。
From the lesson
第一講:陳子昂——「陽違陰奉」的復古派
對於初唐時期最重要的詩人陳子昂,一般都只強調他的復古理論與貢獻,並認為他是掃除六朝浮華詩風的大功臣,將唐詩注入風骨興寄、導向抒情言志的方向。本週課程將重新檢討這個文學史的常識,他究竟是對六朝完全揚棄,還是有更深層的認知?其次,李白身為復古思想的繼承人,如何延續復古思想,又如何在中唐的「李杜優劣論」中成為被批評的對象,而杜甫、韓愈又如何提出平議,都和「復古」這個主張有關,本週課程將重新解析它的相關論題及意涵。
Taught By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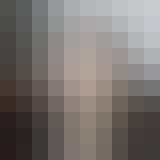
歐麗娟
教授 (Professor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