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課程對象為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同學。 課程目的為通過四個不同特色的主題,討論中國文化的四個主要面向。每個主題選取兩篇經典文本作為核心閱讀,並與延伸閱讀做互文探討,以新角度解讀經典文本的意義,展現中國文化的複雜性、多元性。文本難度與大學一年級國文程度相當。
第二部分

Loading...
Reviews
4.9 (43 ratings)
- 5 stars93.02%
- 4 stars4.65%
- 3 stars2.32%
Taught By

Prof. Ou Fan Leo Lee 李歐梵
Sin Wai Kin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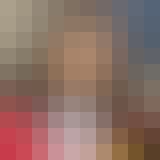
Prof. Wai Tsui 徐瑋
Assistant Professor

Prof. Lik Kwan Cheung 張歷君
Assistant Professor
